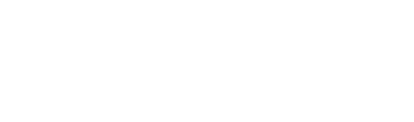案情簡述:A為獲許可從事博彩信貸業務的博彩中介人。於2007年9月,B應其僱主C的指示到A所持有的企業 “X貴賓會” 提取港幣200萬的現金,並將之交予C指定的士人。經多番追討不果,A隨後以一張由B簽名的金額港幣200萬的提取賭場籌碼單為執行名義,針對B提起要求支付一定金額的執行之訴。
B對執行之訴提出異議,理由為B受僱於C,而B於相關貴賓會簽出款項時是經C同意並由C承擔相關債務責任,即C才為真正的債務人;B亦指出簽出款項時的企業已於及後更名為“A”,且更名數月後便不再於相關酒店營運,因此A不是債務關係的主體。 初級法院作出審理,主要就着債權人及債務人身份分析本案所涉及的問題。針對債權人身份方面,重要的是誰為從事商業活動的 “企業” 的持有人,為此,涉案企業之更改名稱並不影響A為相關借款單的貸款人;而在債務人的身份方面,由於B是受僱主C所託到 “X貴賓會”提款,而事實亦顯示“X貴賓會”知道B是代表C取款的。故此,借貸關係是發生在A與C之間,異議理由成立。
A不服,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指出原審判決沾有已證事實間矛盾、在審查證據時存在錯誤的瑕疵,因而出現適用法律上的錯誤,故依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99條之規定就事實方面之裁判提出爭執。 中級法院合議庭對案件作出審理,首先指出立法者為《民事訴訟法典》第599條規定的 “就事實方面之裁判提出爭執之上訴人之責任” 訂定了特別的制度,當中第1款a)項所要求指出的 “具體事實事宜之特定” 界定了以爭執事實事宜為標的的上訴範圍;而第1款b)項所要求的“具體證據方法之特定”以及第2款所要求的 “指明以視聽資料中何部分作為其依據” 則是為着指明所聲稱的矛盾,並尤其作為上訴法院進行重新審查的基礎,即使上訴法院具有同一法典第629條所規定的對所有相關證據進行調查的權力。
正是基於該界定性的功能,法律規定直接駁回上訴作為那些沒有遵守“就事實方面之裁判提出爭執"時須符合之要件的處罰,換句話說,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99條第2款最後部分,相關的部分即予駁回,而無任何彌補的可能性。合議庭強調,上訴法院沒有義務重新審查所有已由原審法院調查及分析的證據,而僅僅是重新審查那些上訴人認為存有錯誤或漏遺之證據且已由其具體指出者(尤其指出在相關庭審錄音中之何片段),並同時指出其認為從該等證據應作出之認定。
由於本案中上訴人沒有遵守就事實方面之裁判提出爭執所應遵守的負擔,尤其沒有於陳述中特定指明證人證言之轉錄內容屬庭審錄音中之時間片段,中級法院合議庭針對此部分之上訴予以駁回,完全及一致表決確認第一審之裁判及其依據,因而裁定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A仍然不服,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主張其上訴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599條所規定的形式要件。終審法院作出審理並指出,針對同樣的問題,終審法院已於2017年3月24日的第85/2016號案的合議庭裁判發表了相關見解。在本個案中,上訴人已確切、具體及明示地於其陳述中特定出作為爭議目的的“事實點"、原審法院合議庭對相關事實之答覆、依上訴人的意見認為應該作出的答覆。
針對指出“具體證據方法"方面,法庭同樣認為相關的形式要件已符合:上訴人對證人證言作出了轉錄便已足夠;不應要求過度的形式主義,而應該嘗試使實質真相優先,否則將導致阻礙任何對事實事宜提出爭議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理由成立,命令卷宗發回中級法院以作出審理,可參閱終審法院第134/2021號案的合議庭裁判。 以上案件所帶出的問題在於分析A是否已符合“就事實方面之裁判提出爭執之上訴人之責任"中所規定的形式要件,從而其上訴應獲接納或予以駁回。
須分析《民事訴訟法典》第599條所規定的形式要件背後之理由:根據相關的學說,上述條文規定之理由是基於訴訟合作及善意的結構性原則,為着避免擴大了上訴法院可以認知的權力、對第一審法院決定作爭議的可能性、以此作為拖延訴訟的手段或延遲正確無誤的裁決成為確定。 考慮到上述理由,應要求上訴人明確、清晰及確定地指出其與法院有不同理解的具體事實點,且透過明示特定出具體的證據以說明相關的爭議。此等形式要求使確實重新審查有爭議的具體事實點成為可操作,這樣能避免加重上訴法院之負擔、倘有的拖延導致司法資源的浪費,以及體現訴訟上應遵從的合作及善意原則。然而,不應對此等形式要件作出過度解釋,否則將導致當事人的訴訟及實質利益受到不合理之損害。 參閱終審法院第134/2021號案的合議庭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