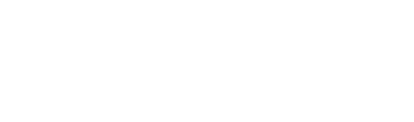案情簡述:A於1998年出生於澳門,其出生記錄載述:父親為澳門居民B,母親為中國內地居民C。由於A符合成為澳門居民的條件,因此身份證明局根據當時生效的第6/92/M號法令第5條第1款的規定向A發出了澳門居民身份證。2005年,A的上述證件獲換發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有關證件分別於2010年和2015年先後獲兩次續期。 2019年,B以家庭團聚為由替其配偶C申請來澳定居。為着核實有關狀況,身份證明局分別對B和C進行了聲明筆錄。C在作出聲明時表示其在1994至1995年間曾在福建與另一名男子D結婚;其後在來澳工作時與B結識並在澳門同居,但未曾與B進行結婚登記或舉行婚禮。
C還表示其現時育有一兒一女,分別是E和A,但並不清楚此二人的生父究竟是B還是D。B和C均表示同意與E和A進行DNA親子鑑定。 由於對A和B之間的父女關係存疑,因此在A於2020年5月提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續期申請時,身份證明局通知A需提交其與B和C的DNA親子關係鑑定證明書,但多次遭到A的拒絕。為此,身份證明局於2020年9月16日向檢察院要求提起調查父親身份之訴,同時就着事件當中可能牽涉到的刑事犯罪行為作出檢舉。
另一方面,身份證明局於2020年9月23日中止了A的澳門居民身份證續期的行政程序,直至法院就B是否為A的親生父親作出司法裁決為止。A不服,向行政法務司司長提起訴願,但其後被駁回。 A仍不服,針對行政法務司司長的決定向中級法院提起了司法上訴,指責被上訴行為違反了合法性原則和適度原則,繼而存有違法的瑕疵。 中級法院合議庭對案件作出了審理,其完全同意檢察院的意見,後者指出本案中行政當局中止有關澳門居民身份證續期程序的法律依據是第23/2002號行政法規第28條第1款和《行政程序法典》第33條第1款,但行政當局對這兩條文規定的適用均存有錯誤。
首先,針對第23/2002號行政法規第28條第1款,雖然此條文規定“當身份證明局對申請人所提供的身份資料的真確性存疑時”,可通知申請人提供其認為必要的補充證明,但實際上,對於上訴人父親的身份不可能存在任何正當合理的疑問。根據《民法典》第1652條的規定,A與B的父女關係經已確立,這一關係通過民事登記法律所規定的方式(即A的出生登記)得到證明,而《民事登記法典》第3條第1款的規定“以民事登記作為依據之證據,不得以其他證據推翻之”,除非是在涉及婚姻狀況或登記之訴訟中;然而,在本案情況中調查父親身份之訴直到目前為至尚未被提起。
因此,面對B是A的親生父親這項通過唯一可行的法定方式予以完全證明的事實,行政當局的任何疑問均是不正當的。 至於《行政程序法典》第33條第1款,根據此項規定中止行政程序的前提是存在一個或簡單或複雜的行政調查活動,然而發出澳門居民身份證並不是一項《行政程序法典》第110條所定義的行政行為。根據第23/2002號行政法規第23條(一)項的規定,澳門居民身份證在因有效期屆滿而失效的情況下須予強制更換,而不需要進行任何更多文件上的調查。
因此,面對由澳門居民A提出的一項續期居民身份證的申請,行政當局只能在履行完相關法律條文所規定的行政手續之後予以續期,發出新的證件,除此之外沒有其他選擇。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認為,行政當局中止相關行政程序的做法不但違反了《行政程序法典》第33條第1款的規定,而且也違反了第8/2002號法律第3條第1款的規定,因而裁定司法上訴勝訴,撤銷了被上訴的行政行為。
我們同意中級法院及檢察院之理解。從第8/2002號法律第3條第1款結合《澳門基本法》第24條之規定可以看到,獲發澳門居民身份證是澳門居民所擁有的一項基本權利,只要一人具有居民的身份,行政當局就有義務向其發出澳門居民身份證。此居民權利亦應包括提出將居民身份證續期之申請,屬已獲發居民身份證之澳門居民所擁有的一項權利。故此,面對這項居民的權利,於行政當局而言僅存在一項作為義務。
行政當局並不需要預先作出一項確定利害關係人法律狀況的行政行為,或作出任何某人具有獲發居民身份證及將有關證件續期之權利的宣告,其僅須單純地遵守官僚性質形式手續,發出身份證或將其進行續期,而沒有進行調查的義務。 當然,行政當局可以對個案中的當事人的居民身份透過法律途徑提出質疑,在確定案件當事人並非澳門居民所生後,開展取消澳門居民資格的獨力程序;但由於在上述的具體個案中相關訴訟(調查父親身份之訴)仍然沒有被提起,故面對一個沒有被質疑澳門居民身份的當事人的身份證續期要求,行政當局只可以進行續期手續。 詳情請參閱中級法院第28/2021號案的合議庭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