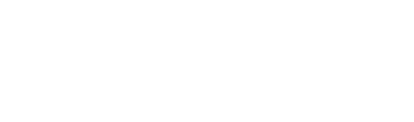案情簡述:嫌犯A從事房地產經紀業務,知悉好友B的4個樓花單位資料及銀行帳戶號碼,先後數次冒充B的業主身份,物色犯案目標再虛稱以較低的價格出售上述樓花單位,藉以騙取買家的訂金。為成功實施上述計劃,以及掩飾有關騙款的不法性質和來源,尤其是有需要在行騙過程中向買家訛稱有關訂金是直接入數至單位業主的銀行帳戶,以獲取他們的信任,嫌犯A便向B請求協助,謊稱由於有朋友急需款項,但基於其本人為低收入人士,一旦接收如此大額的金錢,很有可能會被當局調查,且亦擔心該等金錢會被凍結,遂要求B借出其銀行帳戶替嫌犯A接收有關款項,並隨即將之轉至嫌犯A所指定的帳戶內,對此要求,B相信其因由並同意提供協助,於是便欲透過其本人名下之上述港元帳戶替嫌犯A接收款項,再隨即滙至嫌犯A所指定的另一銀行帳戶。
犯案期間A多次向他人表示認識四個樓花單位的業主B,並訛稱該業主正欲以低於市價15%的價格出售該等單位,又將樓花單位的預約買賣合同及圖則照片傳送予他人,表示同意進行上述交易,接著,嫌犯A便續向不同人訛稱該業主要求其先交付港幣二百萬元作為訂金。為此,嫌犯A便藉工作之便利用公司的物業單位臨時買賣表格式合同,並自行填上虛假內容並交予對方簽署,又訛稱業主現時不在澳門,其之後會將合同交給業主簽署。
由於B多次已多次幫助A進行巨額轉帳,經與友人商討和諮詢意見後認為有關轉帳行為並不尋常,於是便予以拒絕且稱會將有關已入帳的款項全數退回。最後一次嫌犯A便向買家訛稱由於銀行帳戶出現問題,要求買家以現金支付訂金,買家有感現金交易危險,便拒絕之,嫌犯A續遊說買家,訛稱該業主還會簽署委託書及授權書,以保證交易安全,於是嫌犯A私自製作一份“授權委託聲明書"並冒充B簽署作實。
初級法院判處A三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同一法典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鉅額詐騙罪」,五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及兩項第3/2017號法律修改之第2/2006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3條第1款、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清洗黑錢罪」。
A不服並上訴,中級法院合議庭認為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的犯罪性質不同,兩者各自保障不同的法益。詐騙罪是以保護財產免受侵害為目的;而偽造文件罪則旨在保護文件本身所具有的公信力及其在證明力方面的安全性及可信性。然而,本案中所涉及的文件是樓宇買賣合同,單位業主授權委託確認書等,該等文件並不具有獨立性,只能用於本次犯罪行為。因此本案中,偽造文件罪是一個手段,而詐騙罪是目的,兩罪之間屬於想像競合的關係,而偽造文件罪應被相關詐騙罪吸收。故此依職權開釋上訴人被判處的五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
我們同意中級法院的上述觀點,雖然A有偽造臨時買賣表格式合同及授權委託聲明書,但該目的皆是為了順利進行詐騙他人的手段行為,並且只有在該犯罪行為中使用,因此根據刑法理論,A的行為雖然符合「偽造文件罪」的構成要件,亦應被目的行為之「詐騙罪」所吸收。
誠然,對於「詐騙罪」是否應吸收「偽造文件罪」這個問題,本澳司法界目前仍然存有爭議,中級法院亦有法官持有與上述裁判相反的立場,認為由於兩罪法律條文所保護的法益不同,兩罪為實質競合。
然而,倘若相關文件僅為了作出詐騙而偽造,在實行詐騙行為以外沒有其他用途,我們傾向認為應僅視偽造文件為一個單純手段,不擁有獨立性,故應僅判處一項「詐騙罪」。當然,倘若偽造文件不僅僅是實施詐騙的手段,被偽造的文件可用作其他用途的話,由於兩罪所保護的法益完全不相同,那麼兩罪便確實存在實質競合的關係。
參閱中級法院第253/2020號的合議庭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