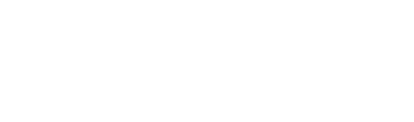2016年,A向B借出多筆款項,為保證A的權益,B將其所持的多個物業的權利通過授權書授予A,其中包括X單位。由於B未能按承諾還款,A於2016年12月2日針對B向初級法院提起了執行程序,要求B償還總額16,557,328.52澳門元的欠款。2016年12月13日,B、C及D置業公司訂立了樓宇買賣預約合同之合同地位讓與合同,B將X單位的預約買受人地位轉讓給C,並取得了D置業公司的同意。此前,B已於2016年12月2日及12日分別向C所持之公司或其本人轉讓了B的其他物業之合同地位或資產。2016年12月15日和2017年1月5日,初級法院命令假扣押X單位。A於是針對B、C及D置業公司提起訴訟,初級法院民事法庭審理後,於2020年6月29日裁定A所提的多項請求包括債權人爭議均不成立。
A不服,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認為B原先聘用的訴訟代理人與C所管理的E律師事務所有明顯的職業聯繫,故B作出有關轉讓行為前,C清楚知道A和B之糾紛,而C取得B之資產及合同地位正是為了協助B“避債”。
中級法院合議庭對案件作出審理。合議庭指出,原審法院認為未能證實“C是否知道A和B之間的債務衝突”以及“C是否知道簽訂相關合同會令A針對B的主張未能得到滿足”是違反了一般經驗法則,沒有全盤考慮其他存在的事實而作出應有的事實推定。卷宗資料顯示B是E律師事務所的客戶,於2016年11月24日簽署相關授權書委任3名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而C為E律師事務所的管理機關成員。根據已證事實,自B簽署相關訴訟代理授權書的短短十多天內,C或由其管理的公司已購買了B的三項資產/權利。合議庭不認為這些交易只是巧合碰上B和A之間的債務糾紛,相反,從相關交易時間中,可以合理推定C是基於其E律師事務所管理機關成員的身份知悉了B和他人有錢債糾紛,而其作為律師事務所管理機關成員,必然對相關法定追討程序有一定認識,可預見債權人為保障自己的權益,將提起保全措施。
因此,C在作出相關交易時,是可預見相關行為將削弱B債權人的財產擔保,令相關債權不可能獲得全部支付或使該可能性更低。基於上述原因,合議庭裁定廢止原審法院對上述兩項事宜的裁判並作出變更。而根據前述變更的事實裁判及其它已證事實,本案符合《民法典》第605和607條所規定債權人爭議權的構成要件,即債權先於交易行為,債務人沒有證明擁有等值或更高價值之財產及取得人C在作出相關交易時知道有關行為將有損A的權益而存在惡意。因此,B和C的預約買受人合同地位的轉讓對A並不產生效力。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A的上訴部分成立,改判A的債權人爭議權成立。
行使債權人爭議權旨在使受爭議的行為對債權人不產生效力,從而保障債權人的債權擔保和避免削弱債權人最終獲得債權受償的可能性。澳門《民法典》第605條及續後條文對債權人爭議權作出了相關規範,當中規定債權人對可引致削弱債權之財產擔保且不具人身性質之行為,得行使爭議權,只要債權之產生先於上述行為(或後於上述行為但該行為須係為妨礙滿足將來債權人之權利而故意作出),以及因該行為引致債權人之債權不可能獲得全部滿足或使該可能性更低。
為此,對於是否出現削弱債權之財產擔保的情況往往很難舉證,故我們同意中級法院的觀點,在考慮取得人在作出相關交易時是否知道有關行為將有損債權人的權益,除了在普遍訴訟的情況下要求證據,特別是書證外,更要以經驗法則角度去考慮,因為債權人爭議權往往伴隨著虛偽行為及合謀的發生,此時過於苛刻要取得實質書證並不現實,亦很難取得,所以立法者在《民法典》 第 344 條第 2 款及第 3 款規定,容許以“人證” 證實債權人爭議權的存在,再結合事實推定及一般經驗法則,就著具體個案作出考量。
參閱中級法院第53/2021號案的合議庭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