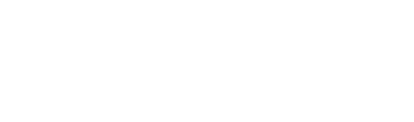相關案情簡述如下:
2018年7月5日,甲為戒掉賭癮而向博彩監察協調局申請參與幸運博彩娛樂場「自我隔離」計劃,為期2年,計劃內容是申請人在隔離期間禁止進入或逗留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全部幸運博彩娛樂場,倘違反禁令,則構成「違令罪」,甲在有關申請表上簽署確認。同日,博彩監察協調局研究調查廳廳長行使局長所授予之權限作出批示,命令甲自2018年7月10日起至2020年7月9日為止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娛樂場,如不遵守有關命令,會被視作觸犯「違令罪」,並於同日向甲發出通知書。有關通知書的內容已向甲作出解釋,甲在清楚知悉有關通知書的內容及若違反有關命令將會承擔的刑事法律後果後簽署確認。
2019年1月1日晚,甲進入澳門某娛樂場。之後,甲在該娛樂場的帳房兌換籌碼時被揭發其在禁制期間內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內的娛樂場。初級法院經審理後,裁定甲被控告的一項由第10/2012號法律《規範進入娛樂場和在場內工作及博彩的條件》第6條第1款、第12條(二)項結合《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違令罪罪名不成立。初級法院的理解是,在自我隔離機制上,該項措施需經行政當局(博彩監察協調局局長)審批只是單純屬形式上的,法律留給行政當局審查空間不多,如非違反法律行政當局需予批准。因此,行政當局實在沒有自由裁量權,只是順應(落實)當事人的意願。
檢察院不同意初級法院的理解,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檢察院的依據是,雖然自我隔離雖然由當事人提出,要實現禁令的產生,必須得到行政當局(博監局)作出一個行政行為的配合才可實現。換言之,只有在行政當局就該特定申請作出許可的行政行為後,禁止進入娛樂場的禁令才能夠出現於真實的法律秩序中,而非行政行為只為著執行當事人意願而存在,當事人發起自我隔離措具有法律依據和限制,也是並”單純”僅由當事人的意願而成就。
檢察院引用立法會審議10/2012號法律的意見書,認為自我隔離機制立法上,是一項劃時代以澳門本地區特有的社會博彩特質而創設的法律,包括人性化的設置、當事人的意願、行政當局的介入、公權力的實現。其中尤為重要的是,若當事人明顯刻意違反已生效的禁令時,實在不能說其背後的妨害公共當局法益沒有違反,因為實已損害了行政當局為著防止病態賭博而付出的努力,只不過這種努力有著過多的人性化設置而已,故認為初級法院的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
中級法院對案件作出了審理。中級法院合議庭認為,第10/2012號法律第12條(二)項所指的行政決定,是實質的行政決定,而非形式上的行政決定。行政決定,除了“合法性”和“正當性”之外,亦須同時滿足“強制性”和“單方性”的要求。此外,第10/2012號法律第6條第1款所規定的“應請求禁止進入娛樂場”,亦必須還要同時滿足了“強制性”和“單方性”的要求,方為實質的行政決定,對其之違反方有可能構成違令罪。然而,在本案中,可以看到只是行政當局對被上訴人個人的協助,尚不觸及公共利益,透過涉案“應請求禁止進入娛樂場”的禁令協助被上訴人遠離賭場,預防其成為病態賭徒。這是協助執行申請人的請求,對其作出幫助。可以說,這一禁令是對請求人的嚴厲的誡喻,對其之違反不應以刑事違令罪論處。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檢察院之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我們同意中級法院的理解。首先,《刑法典》中違令罪是旨在保護有權限機關所發出的命令能有效得以落實,是保障公權力。然而,只有在個人的行為對公共利益造成危險時,個人的利益或自由必須讓渡予公共利益,個人的利益方能被公權力約束。本案中,「應當事人請求禁止進入娛樂場」是以申請人個人利益而成就,是為了保障個人利益,對有關行政命令的違反尚不涉及公共利益,不應以違令罪論處。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按照目前的司法見解,「自我隔離」計劃似乎無達到當初所預期的特別預防功能。本來計劃是為了給予申請一個嚴厲的誡喻;然而,按照第10/2012號法律的規定,違反應當事人申請禁止進入娛樂場的禁令,並不會導致任何法律後果的產生,很難說可以達到開展有關計劃的目的。事實上,我們認為對於違反這類型的禁令,法律應該規定相應處分,即使不應以刑事犯罪論處,仍應該規定行政方面的處分,例如罰款或強制履行一些治療措施。誠然,面對目前的法律真空(對上述違反沒有任何法定後果),立法者理應儘快修法,明確規範相應的違反後果。
參閱中級法院第255/2020號案的合議庭裁判。